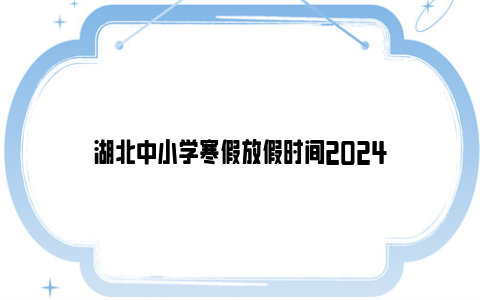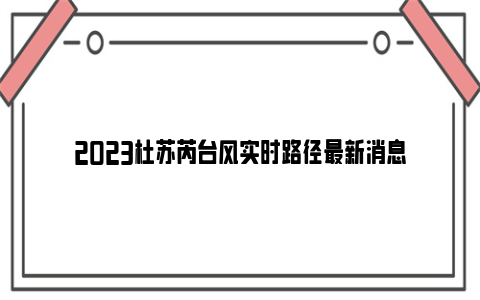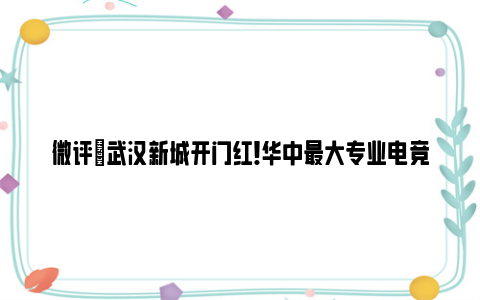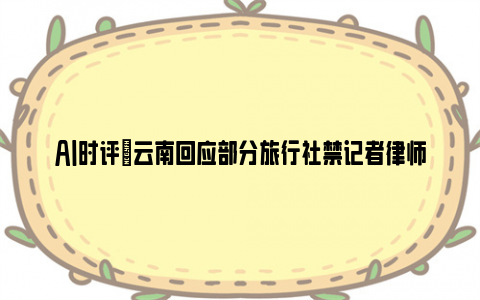著名学者陈西滢早年留学海外10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执教长达20年之久。1942年惜别学界,踏上仕途。1946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驻英国的代表。1970年客死英伦。10年欧风西雨苦砥砺,20载教坛耕耘育桃李,30秋政坛纵横捭阖系苍生。这就是陈西滢。
陈西滢在20载教坛耕耘的岁月里,其中有10年是在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任上,他很有见地地把武汉大学文学院管理成当时中国同类院校之中的佼佼者。10年珞珈,岁月流光。
受惠书香
陈西滢,原名陈源,字通伯,西滢是他的笔名。1896年生于无锡一个优裕的书香门第。父亲陈育在其表弟吴稚晖的影响下,曾在无锡创办了第一个新制高、初等小学。其母杨文贞,为造船厂主女儿,知书达理,颇具大家风范。这个弥漫着浓郁文化气息的家庭,为陈源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三四岁的时候,陈源跟着父亲去小学小班里旁听,接受启蒙。在幼小的心灵就播撒下了知识的种子。
1898年前后,他的父亲与他人在上海的望平街开设了中国第一家新制书局——文明书局,并在汉口等地设有分局。后又在上海办文明小学。这样,陈源就随父来到上海,入文明小学就读。后入徐家汇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附属小学堂,1911年毕业考入商船学校。
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的表叔吴稚晖受孙中山先生邀请,从英国返沪,共策建国大业。吴稚晖见到离别9年的表侄陈源已长大成人,就劝表兄送陈源去英国深造。二月的上海,冷意袭人,在吴淞码头,陈源和家人依依惜别。这样,16岁的陈源离别故土家人,踏上了漫漫求学之路。
1912年春,陈源到达英国,入爱丁堡中学,后进爱丁堡大学。毕业后转伦敦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21年获博士学位。他的文章曾受到威尔斯、罗素、萧伯纳等英国学者赏识。在伦敦时,陈源常撰文申辩或驳斥英国报纸对中国的污蔑不实之词的报道。虽身栖他乡,但心系故园,赤诚爱国。
1922年,陈源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回国担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时年26岁。后被委以英文系主任的重任直至1929年。
1924年,由陈源、王世杰等主编的《现代评论》周刊问世,沉闷的国内学界为之一振。《现代评论》主要刊登政论、时评等文章,同时也发表一些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作为主编,陈源自不甘寂寞。他在《现代评论》上自辟“闲话”一栏,对当时政事、人物、风俗、文化进行评论。文章敢于直言,批评中肯,又不失中庸之道,颇为文坛瞩目。在《现代评论》上,他共讲了78篇“闲话”,后来集其中74篇为《西滢闲话》出版。《现代评论》是文学青年活跃的舞台。后来的文化名人如胡也频、沈从文、凌叔华、李健吾、吴伯箫、施蛰存等都得益于《现代评论》的栽培。《现代评论》之于中国社会,在今天仍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后来1945年他在巴黎的时候,有些人不知道陈源就是当年活跃于《现代评论》周刊的陈西滢,竟多次当着他的面议论鲁迅、刘半农和西滢的笔战。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是合上双眼,叼着烟斗,气定神闲,静静地聆听,就像在听人讲述遥远年代与己完全无关的故事。
1924年5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兼英文系主任的陈源担任接待,也就是这次,他认识了后来的夫人凌叔华。凌叔华出生于官宦人家,祖籍广东,精于文章,工于书画,才华横溢,品貌不俗。1927年,两人结为伉俪。
20世纪30年代,陈西滢(圈中)、凌叔华(前排右二)夫妇与胡适(前排右四)、苏雪林(前排右三)等合影
珞珈岁月
1929年5月,陈西滢应好友王世杰之聘,接替闻一多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其夫人凌叔华一同前往。当时二人对武汉这个城市不看好,认为这是个不宜久居的地方,凌叔华更希望到法国去,以使自己的绘画得到发展。
不久,凌叔华的故交好友袁昌英(杨端六夫人)、苏雪林(张宝龄夫人)分别于1929年、1931年来武汉大学任教。使陈西滢与凌叔华的生活有了丰富的色彩。苏雪林曾在法国学画,与潘玉良是同学,与长于书画的凌叔华灵犀相通;袁昌英是文学家。她们的到来,使一度感到孤单郁闷的凌叔华多了交心抒志的同道。陈西滢、凌叔华最初住在武昌昙华林,1932年,武汉大学新校址在东湖之畔的珞珈山落成,陈西滢和凌叔华夫妇搬到美丽的珞珈山,住进了一幢绿树掩映的小楼,陈西滢为小楼起了个意蕴深涵的名字——“双佳楼”。后有学者为陈西滢、凌叔华编有散文合集,起名《双佳楼梦影》。
珞珈山乃武汉风光秀丽之地,山势舒缓而曲径通幽,临湖瞰江而气象生动,在这里,面对山光,眺望水色,都往往有诗情画意融入胸怀。陈西滢夫人凌叔华与袁昌英、苏雪林常在此谈诗论画,说文解字,营造出了人文与环境的谐趣,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时有“珞珈三杰”的美称,名噪一时。
1931年,陈西滢、凌叔华夫妇在武汉生下他们唯一的女儿陈小滢。陈小滢从小立志要当医生,最后还是从文。她的夫君秦乃瑞博士是英国汉学家和外交官,他们曾为中英友好而作出过贡献。陈小滢和蔼,大方,诚恳,聪明,谈吐不俗,常能切中事理,颇有乃母风范。
陈西滢在武汉大学主持文学院院务工作长达10年之久。在武汉大学期间,他不拘一格,延揽人才,其中有刘永济、刘博平、朱光潜、吴其昌等名家,也有沈从文、叶圣陶等没有读过大学的人。
陈西滢虽受过多年西方文化熏陶,但他却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他认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学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与光彩,是世界文化史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不希望自己培养出的学生学会了外国文学而丢掉了中国文学,到后来甚至于落到邯郸学步的尴尬处境。当时全国并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陈西滢为外国文学系的学生拟定了这样的教学计划:每个学生必修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哲学概论、伦理学等等,每年可以选修一两门中国文学的课程。陈西滢的这种通识教育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在武汉大学,陈西滢为学生开设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世界名著、英国文化等课程,因经纶满腹而得“通儒”之称。在翻译理论上,他在严复“信达雅”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三似论”,即“形似、意似、神似”,一时被奉为圭臬,影响深远。所谓“形似”就是“直译”;“意似”就是“要超过形似的直译”;“神似”就是“独能抓住原文的神韵”。在教学之余,陈西滢还为汉口《大光报》撰写时事专论。
陈西滢主持学院工作很有见地,他管理的武汉大学文学院在当时成为中国同类院校佼佼者。他忠于职守,稳健清醒,见识卓越,具有优秀管理人员的品质。1932年前后,作为文学院院长的陈西滢,常在各种“纪念周”上发表讲演。他的讲演不谈空泛,而是贴近大学生生活的实际,有很强的指导性。如《怎样做笔记》,他不仅在理论上阐明做笔记(听讲笔记、读书笔记)之重要,而且以一些成功名人的例子作为佐证,同时传播行之有效的经验与灵活多变的方法。在《谈学习外国文》中,他强调要打破闭关自锁,必须要学外文,才能汲取西方的文明,还别出心裁地提出学外文的四字诀:“看、读、说、作”。教导学生“工欲善其用,必先利其器”。要读外国文的器具(啃字典)。1934年他在《读书与环境》中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学校在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时期中,创造出这个环境来,不可不说是个异数。”要学生倍加珍惜,不负国家、社会的厚望。陈西滢的讲演,思接古今,征引古今中外名人的经典故事,语言幽默,深受学生的欢迎。
其实陈西滢口才并不太好,苏雪林说“不过他只是开端难,真正说下去时,艰涩的也就变成流畅了。并非滔滔而下,却是很清楚也很迟缓,一句一句地说出,每句话都透着很深的思想;若说俏皮话则更机智而锋利”。徐志摩在《自剖求医》中这样说:“我的朋友(陈源)……说话是绝对不敏捷的。他那茫然的神情与偶尔激出的几句话,在当时极易招笑,但在事后往往透出极深刻的意义,在听着的人心上不易磨灭的。别看他说话外貌乱石似的粗糙,那核心里往往藏着直觉的纯朴……”徐诗哲写道:“他是那一类的朋友,他那不浮夸的同情心,在无形中启发你思想的活动,引逗你心灵深处的‘解严’,‘你尽量披露你自己’,他仿佛说:‘在这里你没有被误解的恐怖’;我们的谈话是极不平等的,十分里有九分半的时光是我占据的,他只贡献简短的评语,有时修正,有时赞许,有时引申我的意思;但他是一个理想的‘听者’,他能尽量的容受,不论对面来的是细流或是大水。”
陈西滢行事低调,不事张扬,谦逊温和,他任文学院院长多年,就连苏雪林、袁昌英与他共事十余年中,也不知道他拥有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陈西滢喜好藏书和收藏烟斗。珞珈岁月,藏书很多。他对书的印刷、装帧都不感兴趣,因此他的书多为“二手货”。他认为买书是为了“读”,不是为了“看”。他特别喜爱的作家有三位:简·奥斯丁、h.g.威尔斯和阿纳托尔·法朗士。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的母亲和妹妹来到武汉避难。8月,南京遭日机空袭,供职于江苏省教育经费管理处的父亲,受恐吓而得病,不治而殁。他在武汉自己的寓所设置灵堂,早晚祭奠。
陈西滢夫人凌叔华是中国著名作家、画家。原名瑞棠,笔名叔华。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她早期作品是在陈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上发表的。1925年凌叔华的《酒后》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奠定她在文坛上的地位;短篇小说《绣枕》又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五期发表,在文坛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凌叔华随陈西滢来到武汉大学后,一直未停止创作。1935年2月,在武汉主编《现代文艺》。凌叔华在发刊词中写道:“若其让文化永落人后,岂非像蜡制人体模型一样,虽然具有美丽的躯壳而缺少灵魂吗?……我们把这片沙漠造成锦天绣地的乐园吧。”不到两年时间,《现代文艺》便吸引和团结了如苏雪林、袁昌英、陈衡哲、冰心、沈从文、朱光潜、徐志摩、朱湘、卞之琳、巴金、胡适、戴望舒等一大批作家。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1937年10月,武汉大学成立战时服务团妇女工作组,凌叔华积极加入其中,并随工作组赴汉阳鹦鹉洲伤兵医院慰劳抗日伤兵。回校后她写了一篇题为《慰劳汉阳伤兵》的通讯,寄到《国闻周报》发表。1938年3月,陈西滢、凌叔华一同在汉口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4月,凌叔华与胡风等96人联名发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这期间,凌叔华以一个知识女性的良知与热忱关心着抗战,同时也留心观察与体验着后方民众的生存境遇与生活状况,写出了她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中国儿女》,表达了她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义愤和对祖国家园的热爱之情。1938年9月,陈西滢、凌叔华随武汉大学由武昌珞珈山内迁到四川乐山。
家国情深
1940年,重庆国民政府设立参政会,由吴稚晖推荐,陈西滢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后期任中英文化协会会长。1942年,惜别了学界,踏上了仕途。1946年,陈西滢出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驻英国的代表。次年,47岁的凌叔华便带着女儿陈小滢途经美国而抵英,与丈夫陈西滢一同在英国伦敦定居,住在亚当森街14号,开始了他们客居异国他乡的生活。
在英国,陈西滢夫妇曾为李四光回国作了很大帮助。1949年9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李四光被选为政协委员。当时他人还在英国,选举结果一经公布,国民党政府十分震惊,决定无论采用什么手段也要把李四光弄到台湾。就在这紧急关头,陈西滢给李四光突然打来一个电话,说驻英大使郑无锡已经接到国民党外交部的密令,要求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否则随时都有扣留的可能。李四光得知后当机立断地决定迅速回国,而且越快越好。他绕道普利茅斯港辗转瑞士经香港回到祖国。对于陈西滢的鼎力相助,李四光至死不忘,1971年临终前对亲友说:“自己能为国出力,与陈源的救助是分不开的。”
1970年3月29日,陈西滢在伦敦因病去世,享年74岁。凌叔华遵照他的嘱托,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江苏无锡老家,满足了“他用全部的爱永远拥抱自己赤诚热爱的国家”的愿望。
在大洋彼岸的英伦,凌叔华无法用自己的母语写作,除了完成并出版她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之外,便主要将精力与才情倾注于绘画艺术与讲学之中。其中,轰动法国巴黎以及欧洲的一件盛事,是1962年在巴黎东方博物馆举办的凌叔华个人绘画,及她收藏的元明清三代画家如董其昌、倪瓒、陈老莲、石涛、郑板桥等人的作品与文物古玩展览。让西方一睹“一条轻浮天际的流水衬着几座微云半掩的青峰,一片疏林映着几座茅亭水阁,几块苔藓卷着的卵石露出一丝深绿的芭蕉,或是一湾静谧清滢的湖水旁边几株水仙在晚风中回舞”的中国文人画的风采。
客居异国的日子,凌叔华一直思念与眷恋自己的祖国。1972年至1981年,她先后5次回国,遍访祖国的大好河山,作画写文,优美的散文《敦煌礼赞》就是她参观了敦煌石窟后写下的佳作。她的自传体的英文作品《古韵》出版后极为世界文化界关注,凌叔华因此而驰名于国际文坛。凌叔华曾在《古韵》最后一篇的结尾处写道:“我多想拥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是多么幸运啊!”1989年12月,凌叔华终于回到她的出生地北京;1990年3月25日度过了她的90华诞;5月22日在北京逝世。一株兰草散尽了最后一缕幽香……
原创文章,作者:nbdnews,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nbdnews.cn/01/08/52/30556.html